探索当代诗歌地理的归宿与意义(下)
——以《行吟达州三百首》为例
版次:07 作者:2022年06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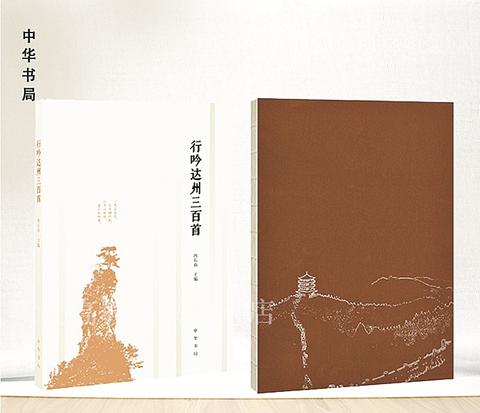
□蒋楠
生命谛视、超越地理意义的人文境界与诗学理想,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巴山诗群复杂的生命意识,构成《行吟达州三百首》丰富多彩的诗歌全貌。对自然、对时代、对家乡、对生活和爱情,诗家们无不以持续的写作动力,吐纳出自己独到的思考与解读。
诗人都乐于观看自然,蓝天白云,美景甘醇。山和水,甚至尘土都有自己的形状,就连风也有自己的形状,它古老、宽广,于隐秘处飞翔,石头在溪流中欢唱,浪花涌入幽深的梦境。“石上铮铮流水奏,分分秒秒未曾闲”(杜括然《峨城山竹海》)“千顷湖浪因风起,十里松声入梦遥”(李德明《明月湖》)“我伴白云云伴我,欢歌牵走画中船。”(张元静《游船》)微波起伏,仿佛有人在云中摇橹。这些诗句,抒情与叙事融为一体,亲切、自然、动人,富于歌唱性,使诗词如华尔兹舞曲般节奏分明。
“晓雾远濛濛,遮断巴渝岭。”郑清辉这首《卜算子·八台山独秀峰》字里行间回荡着追忆的凝重、回眸的苍茫和深思的惆怅。一条蜿蜒延伸的道路,一阵向西而去的冷风,一些看不清的烟雨,它们都在诠释着一座山峰过去发生的一切。在女诗人那里,这种直面历史的烙印也许表现得相对朦胧和委婉,但是,源于历史母体的感受却有增无减,只是带着更加细腻体贴的缠绵之美。
诗词如同果实,其依存于枝头,营养却来自——根脉从泥土中、枝叶从阳光风雨中汲取的丰富元素。没有哪片风景会留恋一个人,但人总是热衷于结伴或独自漫游,寻找从未抵达的地方。并在这个地方成为某个事物的一部分,但又不完全属于它,与它保持适当疏远的关系,不只是从内在的角度看待事物,不断回到一个“我”永远不曾离开的地方。
我始终认为,在众多的石头中,幸运值最高的必定是包裹着美玉的那一块,总在等待揭开谜底的时日。我们有缘敲碎它,就能从中提取出它那沉睡了亿万年的明亮身躯。写诗如同敲石取玉——为了便于记忆,诗家从客观对象中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符号化的语言和方法——这就是“意象”的思维方式与“写意”的造型观。这就引申出本文的另一个话题:把挖掘传统诗词中的现代因素的可能性放在首位,确保地域性和民族特性的延续。
诗词创作多元融合的当代生态
中国古典诗学走向现代,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新旧体汉诗融合,不断深化和升华的过程。
传统诗词,不是小众化的自我标榜,更不是圈内狂欢导致的“集体亢奋”,它应当“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这个“少数人”的最大化外延边界是动态的、不可限量的。
在驳杂的精神博弈与社会运转机制中,相信牵动人类命运与精神力量的,始终还是那种充满爱与温度的书写。书写者应该有更为人性和开阔的视野与更加卓越的创造力,去书写我们的时代与人。
入选《行吟达州三百首》的作品,都是全国诗家达州行和本土诗人的采风作品。采风使诗家眼中的“风景”重新回到对诗性本质和艺术生命的观照上。从固有的模式中跳出,激活了诗家们面对物象的真实感受和艺术演进的多种可能性。
这块元稹生活过,白居易唱和过,李商隐感喟过的古通州大地,随农耕文明走进了历史的纵深处。如今又以格律书页的形式,重现于工业文明领衔的天空。季风拂过唐代诗人的衣襟,八台山风物的吟咏声在时空中飘散,红军站稳川陕脚跟的枪炮声犹在耳畔回旋。而诗家们要借这方水土遗世独立的勇气与骨气,轻抚时光的锋刃,抒发出自己的文气与才气。
从“西南形胜”之地进入,到具体的对景生情或对物感怀,从创作主题的“现实性”到表现手法的“多样性”,都将“应景”的位置放得最低,把文本意趣放到高处,特有的现实氛围使之成为具有区域性元素的诗词范本。无论是外地诗家在巴山大峡谷中找出了一片开阔的地域,寄放自己的心象;还是本土诗家在賨人谷的山坳处发掘了稀罕的泉眼,释放自己的心性。都以变革传统诗词的姿态和行动,力求使作品从象牙塔中走出来面向更多的受众,拓展传统诗词的表现疆域,凸显其社会功能,开拓新的审美境界。
吟诗填词不是随意的行为,是用形式对内容进行规范约束的行为。有条理、有主动性的创作方法,是把发散的思绪记录下来,然后用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把原始素材重新组合在一起。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想到的是工艺。工艺讲究的是完美,每一首诗被创作出来只是技艺进展中的一个过程。在《行吟达州三百首》里,诗家遵循汉诗手工制作传统,装配、打磨、抛光,上漆,注重整体与细节之比例,以和谐之美为出发点,为古典意境的再现开了一扇窗。
“纵使风吹倒,何曾寻靠山。”(何革《八台山独秀峰》)走向黄昏的山谷,唯有诗人才能体察到它的孤独。岁月提供的东西,足可以总结这个世界,诗人还在等待未发生的事情。虽然世界越来越近,但测不准原理,而诗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抵御所有的固定思维。固定思维把人为构建的规范自然化,而诗词创作与这个过程恰好相反——重新审视世上所有的语言和事物。
“道旁新屋花繁树,河岸古榕云蔽天。”(杜泽九《秋游达川百节滩》)百节滩里有诗情,多古意。诗人坐立滩头,读河流这部大书,并把两岸的风物当目录。词幅中的广阔感,拥有不同角度钻石般的多切面,能够自然逼真地还原诗家的情感,即使是微弱的细节,也令读者产生共鸣。
“龙潭龙去只余潭,春日重来兴也酣。”(邓建秋《春游龙潭》)当春日重来,诗人和万物各归其位,并彼此照见。传统诗歌脉络中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但诗家现在的主要实验方向是诗词如何构建空间,空间又如何成为语言的主体。
柳线参差拂小塘,门前大片菜花黄。
——(冉长春《太平村》)
疾步若狂摔一跤,桥边老柳把头摇。
——(廖灿英《回老家》)
江风半堤草,雁字一天秋。
——(谭顺统《野渡》)
心忧日脚西山去,扯根藤藤拽太阳。
——(孙仁权《田家吟》)
川流不息的河水,从古流到今,把庄重的历史和凄美的传说,谱写成一首经久不衰的歌。中国古典诗学最关心的就是通过一首诗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具体的处于现实历史中的主体,而对于诗歌中的历史呈现与身份认同话题显得更为明确。本土诗人想要打破人们对“地域性”的成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用大量富有抒情和独白色彩的语词,和巴渠乡村用语,再现了故乡的种种现实。诗人试图阐释认同的过程比身份重要,认同感与其说是现实,倒不如说是意图,他们的书写发生在与故乡保持一定间距的时刻。也可以这样说:他们并不总是在吟咏达州或在达州吟咏,而是从达州出发来吟咏。
江湖远,也没有故乡远,我们虚构一个航标,带着中国古典诗学遗传的地域性与民族性,踏上装满山峦、村庄、河流与炊烟的船舱,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在转型时代的奔流中逐浪,向着更远的远方。“挤痛西装,挤痛石榴裙。挤痛书包背篓,关不了车门。”(蒋娓《喝火令·挤公交车》)在城市里穿行的公交车,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它承载着人们的身体,承载着一座城市的物质部分,甚至非物质部分。只是诗人的故事换了一种讲法,她把新叙事模式置入这种质朴流畅、清新和谐的审美取向中,找到了自己的韵律和语言风格,也增加了词义空间。
面对社会的发展与转型,中国古典诗学早已驾着时代性的车轮,在没有尽头的高速公路上,驶向没有尽头的群山。高速公路上,唯一让人分心的是从社会现实的低洼处折射出来那些幽深难测的语境意识。其中涉及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问题,包含着传统诗词在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时,所给出的应变能力。
从古老天空中取出鹰骨,制作成骨笛,在越来越模糊的笛音中,我们会想起巴山夜雨的前世,而传统诗词正以“摹古主义”的方式演进。事实证明,传统诗词并没有因现代化进程的碾压而消亡,却由此获得了活力与新生。与此同时,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对传统形式的过度依附,因完满而造成的自足和封闭,导致的艺术评判标准混乱、艺术品格下降等等。因此,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寻找隐入大地的花朵,用传统诗词揭示社会现实的犁耙,翻耕艺术语言的自律,把艺术本体语言推进和现实表现有机嫁接起来,抵达语词的未尽之意。犹如一行大雁站在时空中,要赋予翅膀新的涵义。
高铁呼啸奔向远方,汽车带着一身泥归来。当山脊拖着一把拂晓的斧子掀开天地的澄明,诗家们的心境像秋水一样宁静,共同回望着身后的泥泞。只有摸清中国古典诗词的性格脾性和优劣得失,才能规约其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古典诗学裹挟着那粒天人合一的种子,在时间之河上生根,然后又在千年不断的流水中伸出手臂,于暮鼓晨钟中暗暗发力,在风霜雨雪里绷紧根系,牢牢地将人和自然连接在一起。时间之河更多的是沉默,专注于流水,沉溺于山水的空灵,告解着吟诗作赋的善男信女。古典诗词的精华亦在这里——执着于精神世界的内在省察和人格炼造。我们在这条河的岸上行走,让风帆扬起超越的形而上语境以及形式自觉,气韵、诗境、境界的浪花飞溅。我们要站在生活的顶端,秉持多元、开放精神,以此探索出中国古典诗学向现代性演进的多种可能性,只有具备开放融合理念,才能确保当代性认同,最终完成形式语言与时代精神的最佳配对。
时光一直在前面,河流一样不舍昼夜,它有意无意地提醒,让我们不要停留下来。所幸的是,我们从《行吟达州三百首》这部作品集里可以看出,诗家们一直在努力探索着前行,以顺应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流变。基于古典意象的书写与表达,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复古,而是建立在汉诗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上,对词语本身进行更深的追问。从语言的表层拆解出潜藏其中的情感、韵致、姿态、声音、境界,为传统诗词作品添上更生动的汉语表情。这也表明诗家们在把握汉语的质地和精神之外,始终在潜心创造,以此来保留词语的一次性原则,拉伸起现代性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