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陈忠实 精品为王方正道(下)
——重读《白鹿原》
版次:08 作者:2021年05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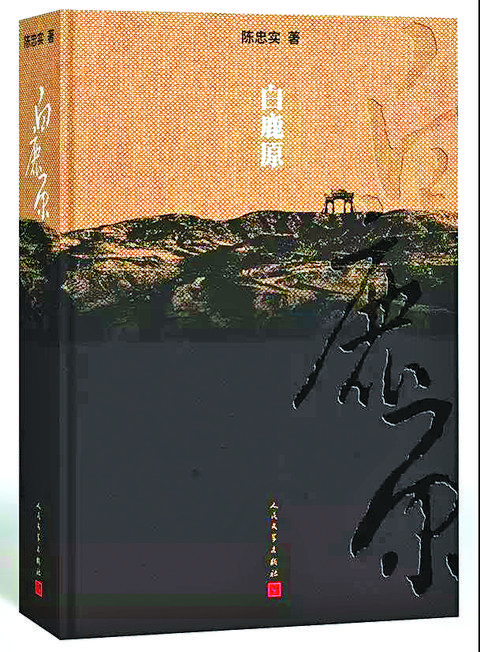
□冯晓澜
三
两个叛逆和浪子,黑娃和白孝文都殊途同归,顺应时代潮流率保安团起义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黑娃是主动起义,白孝文是被迫反正,但最终命运却有天壤之别。这不只是命运的宿命使然,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白孝文卑劣的人格因素,由此,才导致了黑娃的悲惨结局。尽管黑娃在朱先生的教导下,勤读诗书已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仍遭到了白孝文这样无耻卑鄙小人的暗算。白孝文是一个没有明确价值观的人,也有可能是他当初被逼到过绝境,才更知道有权有势的重要。因此,他除了自己,是不在乎别人死活的。他与田小娥厮混时,不管不顾自己的妻儿。他参军时,张团长提拔了他,对他是有恩的,可后来他为了利益,为了功绩,直接朝张团长打了一枪,完全没有一丝犹豫。还有他最后坑了黑娃,也完全没有顾及过去两人的关系和感情。但令人意味深长的是,最后,他当上了县长,反而结局比黑娃好。这就是历史和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人物身上的具体反映。可以说,白孝文这个人物形象也是十分出彩的。
小说中另外两个女性形象,也值得我们关注。同样是封建主义的牺牲品,但她们却是性的纵欲和禁欲的两个活生生的标本。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田小娥,小小年纪即落入作财东小妾的火坑。被欺凌、被压迫、被奴役,人性被摧残,她只不过是给财东干活和被财东泄欲的工具和玩物。黑娃的到来,唤起了她青春的激情、原始冲动的生命力,使她的人性本真得以苏醒并享受到了一个女人应得到的情和性的欢乐。她义无反顾地向凶残、吃人的封建礼教,发起了生命本能的反抗和叛逆。偷情败露,田小娥被一纸休书撵回娘家而臭名远扬。但有情有义的黑娃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苦命的田小娥,带着她回到白鹿原。恩爱的黑娃夫妇,因封建礼教强加的恶名,而得不到民风淳朴的白鹿原的接纳。他们夫妇积极参加了农民协会,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中。在大革命失败之际,黑娃外出参加革命军队的时候,道貌岸然的鹿子霖不顾同祖同宗和作为长辈的尊严,撕下了伪善的遮羞布,借助反革命力量追剿黑娃之际趁火打劫,巧妙地霸占了田小娥。并把她作为与白嘉轩明争暗斗的工具,用她的美色和身体作诱饵,去勾引新族长白孝文,致使整个白氏一族蒙羞,也使田小娥本不清白的名声,更是臭名远播。
田小娥并不是世人眼中的妖妇、荡妇,她没有过多的奢求,追寻的仅是人性中最根本的欲望,只是欲望被点燃而没有节制。这就有了日后,她与黑娃、鹿子霖和白孝文几个男人的牵扯,但是她又有人性中最朴素的善良,在白孝文落难之际给予他同情与关切。她勇敢地争取着生存、人性、自由的基本权利。她何罪之有?她的纵欲是受迫害使然,她是被封建礼教和反动势力一步步迫害致死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鹿子霖是直接迫害田小娥的刽子手之一。不仅如此,鹿子霖还将魔爪伸向了自己的儿媳。儿媳过门后,由于是包办婚姻,儿子在外参加革命长期不在家。儿媳独守空房,守着活寡,鹿子霖的一次酒后失德,轻佻不轨的举止,激发和燃起了儿媳最原始的情欲。当儿媳找准时机,向公公发出求欢的信号时,道貌岸然的鹿子霖却巧妙而严厉地羞辱了儿媳。被长期禁欲的儿媳,被公公撩拨起的情欲之火,焚烧着、煎熬着,又加一场羞辱,终于被逼致疯而悄无声息地凄然死去。她比寡妇的命运更凄凉、更悲惨,她活在无望中,苦守苦熬,过着没有目标如行尸走肉般的生活——一块贞洁牌坊,凝结了她悲惨无告的一生,让一个鲜活的生命,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这一典型的意义,远远超过前者田小娥。它无声地控诉了封建主义残酷压迫妇女、摧残人性、吃人的、杀人不见血的罪恶本质,振聋发聩,撼人心魄。
四
《白鹿原》是一部从反思、寻根思潮中超拔而出的现实主义杰作。《白鹿原》力图展示生活原生态,揭示出纷繁社会中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规律。它通过设置大量看似偶然的事件,把具体的人物命运和宏大的历史进程连结起来,从而使历史呈现出某种浑沌的状态,具有了生命的灵气。
《白鹿原》的寻根主题主要是精神和心灵的寻根,带着对精神中“真”的追求写出儒家文化的精髓,并通过文本中人物的个性描写,来宣传中国文化的深刻价值,表达自己的“寻根”理念。陈忠实的寻根性思考,并不仅仅停留在以道德的人格追求为核心的文化之根,而是进一步更深刻的揭示出传统文化所展现的人之生存的悲剧性。《白鹿原》在以关中人生存为大的文化背景下,展开了一系列的人物活动,粗野朴实的乡村习俗、慎独隐忍的儒家精神,则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来体现的。
《白鹿原》的可贵在于,没有陷入历史的深潭去一味图解历史,而是注重以原生态的生活和细节真实来再现历史,但它又不是纯粹客观地还原生活,而是力图通过各种势力在原上的冲突和发展,揭示出传统文化的命运走向。在写作伦理上陈忠实也并没有坚持“零度情感”,而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做了深刻的思考并以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体现出强烈的爱憎。在陈忠实笔下,男人睿智聪慧、豪侠仗义、勤奋持家、阳刚雄起。有这样阳刚的男人,女人才温良贤淑。但是,民国的革命让这一切发生混乱,有人当了土匪,有人抽了大烟……而陈忠实让这些制造混乱的人,都不得好死,或上刑场,或被暗杀,或被活埋,反正不得好死。这就是大丈夫的爱憎分明,就像水火那样难以共处。
在具体的创作中,陈忠实大量借鉴了潜意识、非理性、魔幻、死亡意识、性本能等现代主义手法,从而使情节愈显曲折,突出了人物命运的不可臆测。现代性的注入,为现实主义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陈忠实正是通过这种魔幻描写,模糊了生者与死者、冥界与人间的界壁,在人与鬼的冲突中来展示人性深处的东西,揭示人性的悲剧、人生的苦难。同时,这种手法还给所叙述的历史带来一种不可预知的神秘性,给读者以心灵上的震撼:仿佛冥冥中有一只巨大的手,掌握着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发展。
《白鹿原》选准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不是单纯的家族小说,而是家族+宗族的宏观叙事结构,从而,立体而鲜活地构成了我国农村最基本的、乡土社会的、文化的、生存的结构状况。它以活生生的人物群像,反映了白鹿原上的风云激荡、历史变迁,既活画出我们的民族魂,也抒写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文化的根系所在,弘扬了中华民族脊梁宁折不弯的伟大精神。正如作家在题记中恰如其分、匠心独具地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话所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这句话不仅高度概括了小说的题旨,无疑也成为我们解读《白鹿原》的钥匙和路标。
《白鹿原》以主要人物白嘉轩心理的发展进程来统率全篇,辐射开来,塑造了白鹿原上人各有别的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构成了一幅关中地区农民生活状态的壮丽画卷。小说对心理结构的把握是恰切到位的。它围绕人物心理的发展而使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得以推进,特别是对性心理的探索和挖掘也是十分成功的。小说中性心理和性爱的描写,尽管引发争议,但细加考察,它不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是融于小说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而成为人物命运进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白鹿原》的性描写唤起我们对生命活力的赞美,对人性倍受摧残的憎恨。它有别于感官刺激的纯“身体写作”,而用生命之力、人性之美,写出了生命中原始的激情和壮美,折射出社会烙印的残酷和暴戾。对性的描写的崇高与卑下、成功与失败,其高尚和粗俗的分野,完全取决于作家是否具有崇高的审美态度和严肃的社会责任感。陈忠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做出了这样的探索,应该说是成功的、严肃的。此后,文坛的“黄货”泛滥,不能不说,是文学成为市场奴隶的悲哀。市场功利的对金钱的追逐,它只是一个表象,从根本上说是我们的作家们失去了社会责任感,成了文字垃圾的制造者。
美中不足的是,陈忠实所追求的高密度的语言叙述节奏,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前几章是高密度的欧化句式较长的叙述语言的探索,后面的章节就不自觉地回到了作家原本风格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影响了风格的统一。当然,瑕不掩瑜,毫不影响它成为一部凝重、博大的现实主义杰作。
大凡成功的探索之作,都会给文学史留下默默前行的足迹并树起一座高峰。1997年12月陈忠实以《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确,当之无愧。
陈忠实写《白鹿原》是受到路遥的“刺激”,当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摘取文坛桂冠之后,1987年已担任陕西作协副主席的陈忠实却销声匿迹了。他只留下一句话:“如果50岁还写不出一部死后可以作枕头的书,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那时他45岁。他为心中的目标,义无反顾回到出生的乡村,耳朵听到的是熟悉的乡音,房屋背后看到的是亲切的土地。隐居苦读苦写多年之后,《白鹿原》一战成名,实现了他“一部死后可以作枕头的书”之宏愿,终于给中国当代文坛奉献出一部足以传之后世的经典巨著。
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六十年长篇小说典藏”,收录了《白鹿原》。2019年,《白鹿原》又入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七十年七十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白鹿原》还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据统计,《白鹿原》累计印量已超过320万册,在国内外读者中反响强烈,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而广受传播。
一本书成就一个作家且在当代文学史占有显赫的位置,陈忠实应该是“一本书主义”以作品说话、以精品为王的践行者和成功者。他写的“一部死后可以作枕头的书”以留传后世之使命担当——自觉的精品意识,在身处刷存在感、以作品数量取胜的当下,无疑具有强烈的警醒和启迪作用:唯有心有读者、心有人民、精品为王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