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副刊
版次:09 作者:2018年11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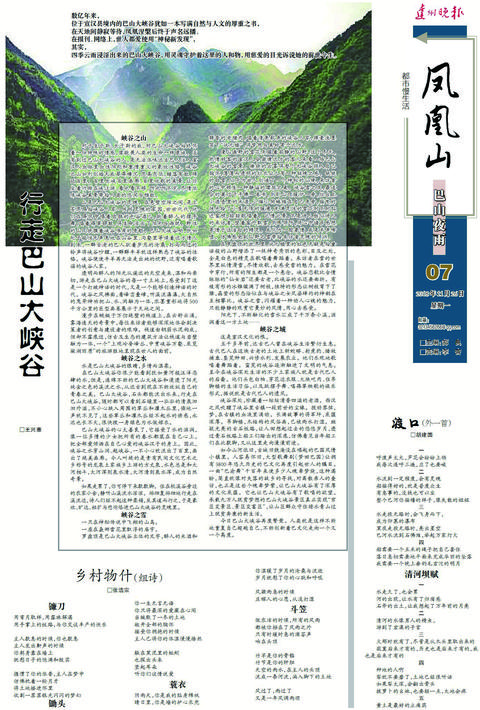

前不久遇见一位从北京回来的往日文友,我们在城后山顶一家山庄吃饭,他得知我还在给报纸写副刊文章后,望着山下万家灯火长叹了一口气说,哎呀,你这个人,或许一辈子就这样写副刊文章了。
这个文友二十多年前是写诗的,后来到外地闯荡,而今是一个写影视剧本的“大咖”,年收入起码有几百万。我明白他对我的惋惜,像我这样一个老古董似的写作者,早就落伍了。
像文友这样对我抱有遗憾的人,还有我老家村里的堂叔。早年他在乡间,我常在本地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堂叔便自费订阅了这份报纸,每逢他看见报纸副刊上有我的文章,便拿着报纸到村里溜达,指着报纸上的文章对人显摆说,这是我侄儿写的。村里有位看古书的老文人,有一天对我堂叔说,在报纸上写那种文章没啥了不起,喊你侄儿写一本像《红楼梦》那样的书出来嘛。堂叔气得胡子乱颤,似乎是受到了刺激,跑到城里对我下命令,你要向曹雪芹学习,写一本《红楼梦》那样的大书出来。后来堂叔又知道有本叫《白鹿原》的小说,就干脆说,你就写一本《马耳坡》!马耳坡是我老家的一座山坡。对我满怀希望的堂叔,而今已长眠在马耳坡下,我到他坟前祭奠,总感觉愧对于他。
我是一个副刊写作者。我蜗居在民间大地上,把那些滴着露水、腾着雾气的文字,投送给报纸副刊,让我的心灵得以栖息。副刊与我这样的作者的关系,其实和好心人把一个流浪的孩子,抱回家,一勺一勺喂养大是一个道理。所以我对报纸的副刊充满了感情。
因副刊写作,我人到中年后话越来越少。这一方面是因为简练的副刊文字所带来的性情改变,另一方面发觉以前每天说的话大多重复,喋喋不休的,往往是别人的人生,与自己无太大关系,索性少说。副刊的文字,因版面所限,容不得那么多废话,一般就是千字文。其实说清一件事,表达透一种感情,有时一千字往往足够。流传千古的那些古诗文,有些还不到一千字,但传递的思想和感情,让今天那些结结巴巴的冗长表达,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也许古人的文字,先是写在龟壳、竹简、羊皮、锦上,后来有了纸张,但成本太高,所以得把话往朴素简单上说,所以古人的文字,才那么凝炼有力。
这些年,因为坚持给报纸副刊写作,让我觉得,在那些发表我文章的城市,都出没着我的朋友。我做最低测算,一篇文章有十个人阅读,一年下来,读者就成群了。所以发表我文章的城市想起来就特亲切。在这个国家报纸副刊写作的大军中,我实在是一个幸运的人。一些很有影响的大报,在它们的副刊上都流淌着我的文字,我甚至没给他们打过一个电话。一位晚报编辑对我说,不要说那么多,也不要和我套近乎,你用文字来说话,就够了。
我出差到一些城市,首先就买几份当地城市的报纸。在每一篇市井新闻里,触摸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以及鸡零狗碎的乐趣。而那些报纸的副刊,我要喝着一杯茶去阅读,好比夏天在山涧、树阴下纳凉的人们,他们要说的东西,往往澄静悠远。一张报纸的名气,在于新闻影响力。而一张报纸的副刊,它是安静的,躺着的,不动声色的,而沉静后的灵魂,往往就是这个形态。有人形容说,副刊是报纸后花园里的私房菜,它像亲人的家常菜一样等着你回家,也是打开一扇家门的密码。
而今,是网络碎片化阅读习惯的时代,报纸的副刊版也大为减少,而大多数人都没有收藏报纸的习惯。这就注定了报纸的副刊,很快会被回炉化为纸浆,成为再生资源。
有一次我去一家老字号理发店,坐在凳子上等,屁股下坐的一张报纸副刊上,就有我写的一篇文章。我突然感觉,那张报纸,像一个流落的弃婴,无人收养。我捡起来,带回了家。
其实像我这样的副刊写作者,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生排毒的过程,是我修为人生的一种漫漫求索。我每天从纸上,从网络上打开报纸的副刊版面,像老朋友那样问候一声:你好,副刊!□晨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