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贴地书写
——贺享雍小镇系列长篇小说读札
版次:05 作者:2025年04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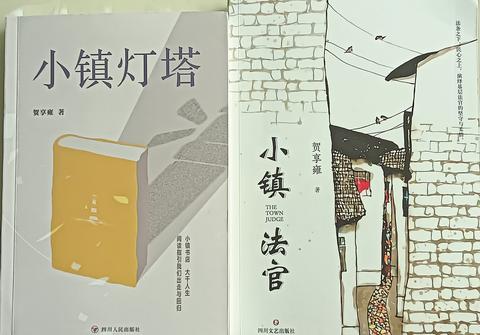
在达州巴山作家群中,贺享雍是一位老当益壮、笔耕不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持续在乡土文学深耕并不断求新求变的小说家。他继十卷本《乡村志》和《时代三部曲》之后,又先后推出了小镇系列长篇小说《小镇灯塔》《小镇法官》。它们均以“小镇”为背景,通过现实主义的贴地书写和人物群像的精心塑造,再现乡镇基层社会纷纭复杂的现实图景。
《小镇灯塔》以“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为主题,以三江交汇的福镇为舞台,以福镇青年范戈响应政府号召回乡开办灯塔书店为主线,讲述他在市场经济与城市化冲击下,坚持推广阅读、重建乡村文化灯塔的故事。小说生动地再现了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扩张大潮冲击下,故乡阅读底蕴逐渐丧失,灯塔书店在逆境中苦苦支撑的现实困境。由此,反映了当下乡村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在时代巨变中,传统文化与阅读氛围受网络、自媒体冲击而逐渐式微之现状,以及主人公执着坚守、传播文化的可贵精神。
主人公范戈回乡开办灯塔书店,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着主客观因素推波促澜的合力驱使:一是受家乡小镇政府招商引资的感召,二是范氏一家从曾祖父始、代代相传钟情于文化传播的家风,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让他立志做一个文化传播的传承人。小说用第一章四个小节,围绕范戈回乡参加“福镇乡友回乡创业座谈会”的经历见闻与家族史的回溯,既展现了小镇风情和人文历史,也为主人公为何要开办书店的行为动机,增加了说服力和可信度。小说如此开篇虽显节奏缓慢,对读者的吸引力有所减弱,的确有些冒险。但作者却胸有成竹,为的是巧妙地将个人理想与时代感召相结合,将文化力量与道德追求相结合,为作品灌注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伟力。小说始终贴着人物和灯塔书店着笔,以范戈这位文化坚守者、传承者饱满形象的塑造来感染打动读者,从而,警醒我们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不能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尤其是在乡村地区,文化的滋养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小说还塑造了一批复杂鲜活、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如与主人公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金珏、到福镇开讲座并签名售书的齐教授、社会底层痴迷书籍的文学青年伍浩、年少无知“出卖”恩人长怀愧疚的书痴黄伯、迷途知返的赌博女受惠于读书而最终成为作家的王明玉、行侠仗义的前警察现出租车司机张学安等。这些人物在主人公范戈对阅读与文化的坚守中,内心的微光被点亮。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体的奋斗与挣扎,更是代表了乡村中那些对文化、对精神世界有着追求的群体。通过这些人物,让我们看到了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下,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望依然存在。这种渴望如同星星之火,有着可以燎原的潜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范戈曾经的同学,现为福镇宣传委员的代光信这一人物形象。他不仅从个人角度为范戈灯塔书店全力相助,而且还成为镇政府与灯塔书店连结的纽带。书店开业剪彩,本来镇政府领导答应光临以显重视,后因要参加重要会议分身无术也就派代光信代劳了。范戈到镇政府请领导参加齐教授在灯塔书店开办的讲座。不巧的是,镇领导不在,范戈委托代光信代请。讲座那天,又遇镇上万紫千红大世界李总的“幸福花园”开工典礼,镇领导自然腾不开身。镇领导重视的是经济发展,对文化建设只停留在口头上,从没有真正给灯塔书店一点关爱。作者就这样通过代光信这一人物,用对比手法之叙事策略,实现了对现实的批判。尽管温和,却充满智慧。作者不回避现实、勇于批判现实的态度,值得赞赏!
贺享雍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乡村的热爱,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乡村文化世界。《小镇灯塔》不仅是一部关于创业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文化传承、精神追求和乡村振兴的鲜活记录,从而,启发读者对乡村文化发展作更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如果说《小镇灯塔》的地理坐标为作者的家乡,那么《小镇法官》的地理坐标悄然发生了位移,将人物活动的舞台迁移到了同属川东地区的烟霞山下的嵇镇。这不只是地理位置的简单迁移,而是体现出作者视野的宏阔和讲好达州故事、中国故事的雄心。
《小镇法官》将聚焦的镜头对准基层司法系统,以小镇法庭的日常运作作为切入点,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基层司法工作的生动画卷。基层法庭舞台小、案件小,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大多时候是与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打交道,很难出成绩,也很难体现出成就感。越是日常琐碎,越考验作者的眼光和功力。所幸的是,作者富有乡村题材的创作经验,从《小镇灯塔》的福镇抽身后,一进入烟霞山下的广阔沃土,他的笔触就显得愈加自信从容而挥洒自如。无论是叙事语言,还是人物对话,都带着鲜活的生活气息,均可圈可点。特别是对方言俚语娴熟的运用,写活了大巴山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气神。
小说结构与《小镇灯塔》以主人公开办书店为主线不同,《小镇法官》采用章回体、大多以人物命名章节,旨在塑造人物群像,但也并非平均有力,而是以主人公金海燕作为穿针引线和团队凝聚力的核心。由此,法庭团队成员,在作者巧妙的安排下先后登场,动态化书写他们的前世今生,然后,汇聚到以金海燕为庭长的温馨大家庭。这个变化,体现出作者去主人公中心化之目的,意在塑造小镇司法工作者可亲可敬的人物群像而非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
事实上,小说也的确实现了作者的预期。小镇法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各自的来龙去脉和在小镇舞台上的精彩演义。金海燕的知人善任、关爱培养下属和忙于工作而与家庭产生矛盾的烦恼;江副庭长快到点的松懈和积极性被金海燕巧妙调动起来后的安心工作并带动年轻人上进的惊人转变;辅警傅小马这个编制外聘用人员的好学肯干,但终未能考上编制不得不离开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去另谋前程的无奈;书记员欧小华、罗娅,这两个“九五后”年轻姑娘,出身和成长环境迥异,也就有各自不同的烦恼,相同的是,她们都勤奋好学,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都有不同的成长。正因为有对人物神形的捕捉和工笔细描以及对七情六欲和忠于职守的细腻书写,才有了这群小镇法官群像如在眼前的栩栩如生。
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小镇法庭里,法官们面临着法与情的艰难抉择,他们的每一次判断都不仅仅是对法律条文的简单应用,更是在人情冷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权衡利弊、追求公平正义的过程,从而,尽力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江副庭长巧断拆迁案。他的巧,一是善于倾听钉子户万大爷关于猪圈所隐含故事即念想的倾诉,满足其情绪价值,找到打开万大爷心门的钥匙,而这念想又事关个别基层干部脱离群众、不问群众疾苦;二是双方对拆迁款各有底线,互不让步,处于拉锯战,江采取变通手法:一场酒席让镇领导放下身段,再辅以借酒席沟通时,一方去拆猪圈,同时提出增加点拆迁款。经江副庭长有理有节、双管齐下的巧妙处理,结果双方皆大欢喜。一桩令乡领导头痛的难事,竟解决得如此出人意料。其症结不正在于思想工作没做到家吗?正如万大爷所说,“早知如此,我还扯锤子个皮!”万大爷的话,令人啼笑皆非而又发人深省。
《小镇法官》通过离婚案、财产纠纷和拆迁等案件,呈现小镇法官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法律冲突中的艰难抉择,同时,穿插金海燕的家庭矛盾与事业挣扎,凸显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智慧与坚守。它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的人物群像和深刻的社会内涵,再现了基层司法系统的真实面貌,为当代文学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由上观之,小镇系列各有自己的主题,以小切口进入、建构并呈现小镇在新时代的风貌。从体量上说,两部均在二十万字内,在长篇小说追求叙事宏大和体量庞大的当下,贺享雍从容回归不再追求庞大与史诗,而是以小镇系列作为反映现实的轻骑兵。因为在碎片化时代,作者难以把握总体,只能以一己之力去接近真相,用一己之长去勘探现实,写出自己对现实的理解、梦想和愿景。小镇系列选材好、结构巧、人物活、语言扎实,延续了贺享雍对现实主义特别是对乡土文学的深耕与拓展,以细腻的笔触揭示社会变迁中的个体困境与集体精神追求。这种对基层普通人物的关注和刻画,体现了贺享雍一贯的创作风格。他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素材,用朴实的文字和精巧的结构描绘出真实的社会景观。与他的《乡村志》《时代三部曲》系列作品一样,小镇系列长篇不仅同样凸显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而且,也体现出对现实主义文学贴地书写,勇于担当时代使命和不断进取的创作姿态。
□冯晓澜